过去数十年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多元化逐渐迸发出来,恰恰在于社会的总体松绑与选择的多样性。
撰文丨连清川
这还是21世纪吗?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赵丹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个田野研究报告,题为《体制分割与青年的婚恋行为和就业选择分析——以东北青年为例》。
大概意思是说,在东北,有没有编制成为了东北年轻人是否能够结婚的强制性前提条件,体制内只找体制内的,体制外的无论男女,有没有钱,都面临婚恋危机。东北青年没有选择,只有逃离。
图/网络
这简直就是逆天的血统论的返祖。
现代社会的重大成就之一,就在于婚恋突破了血统、财产、职业、地域等等加诸于个体之上的重重枷锁,使个人的选择成为婚姻不说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当一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机制性的压迫,使婚姻屈从于职业这个元素的时候,这个社会就返回了旧时代,脱离了现代社会。
可是我仔细咂摸了一下我的个体经验,却不得不承认它不仅仅一直都存在,并且还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劝诱我的子侄辈,在对未来的选择上,要跳出原有的地方,向大城市甚至向全球发展,看更大的世界,追求更大的成就。但我的这些言论,被所有的家人痛斥为幼稚,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好?就在本地考公考编,安安稳稳地过一生,有什么不好?
事实证明,我家人对于孩子们的规划,比我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我越来越不得不承认我的“幼稚”,甚至开始接受,要在国内生存,考公考编,是几乎“唯一光明”的前景。
01
赵丹在他的社会调查里,考察了多种组合。
有编制的+无编制的,没有可能性。他的报告里说,在东北,“有没有工作”这个问题的实质性是:有没有编制内工作。没有编制内工作,就等同于没有工作。谁会找一个“没有工作的人”?
这个定义之严苛,当然超越了当下中国对于工作的定义,几乎是全面性的“返祖”。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里,由于互联网经济的全面发展,电商、自媒体、外卖等行业的急剧扩张,“工作”的定义不仅仅突破了体制边界,而且突破了拥有固定工作时间的限制,自由职业者也已经成为了正儿八经的工作。
而在全球的范围内,“工作”突破地域、时间和收入来源,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趋势。
也就是说,“自由职业”越来越成为职业的主流定义。未来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之下,职业的固定性特征,恐怕会全面消失。
但是这在中国,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一再加强,甚至在东北,重返体制成为了一个趋势。
无编制的+无编制的,这当然理论上可以发生。但是由于全区域的歧视性社会风气,这种婚姻就处于婚恋市场的底端,遭受到社会的鄙视。赵丹甚至说,那些没有编制的未婚青年,甚至放弃了外出社交,以避免亲朋好友对他们的“拷问”。因此,这种婚姻的发生频率,当然只会越来越低。
有编制的+有编制的,这是理想型的婚姻。但是,这种理想型婚姻却有着诸多的潜规则与“食物链”。
“在东北社会,拥有公务员身份的行政编制比事业编更胜一筹,但二者的排序又领先于企业编制。另外,在同一编制体系内部,还存在职务级别的高低排序。”
他在报告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在事业单位中从事公益性岗位的女青年,在公务员体制内举办的一个联谊活动中,连报名都被拒绝,因为她不是“正式入编人员”。
他的结论是:体制对东北青年婚恋的影响力,或许超越了收入、学历、户籍、毕业院校、个人能力、样貌,甚至包括爱情在内的诸多常见因素。
在赵丹看来,至少部分地因为在婚恋市场上,非体制性工作已经使东北青年无从获得满足甚或可能,因此,东北青年大量逃离东北。
“逃离东北”还略带有一丝英雄气概的味道,成为当下越来越多的东北青年反抗体制分割,证明自我实力的积极行动策略。
我对于赵丹的现实洞察十分认同,但对于这个结论却深表怀疑。
统计数据表明,2023年,在全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上,黑龙江、吉林排名仅仅在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之前。把海南的面积和人口规模除外,你可以想象它的状况。即便是情况最好的辽宁,也在最后梯队。全年2754亿元,不及广东的零头。
东北的经济状况不复赘言,在改革开放至今的数十年时间里,东北一路下坠,民营经济长期低迷。去年爆火的《漫长的季节》,讲述东北在国企改革中“开了第一枪”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但是,东北却并没有在率先改革中获得红利,反而成为了牺牲品。
赵丹显然是将因果倒置了。不是因为婚恋问题造就了青年逃离,而是因为无望的社会造就了婚恋的现状。
是经济决定了婚姻,而不是相反。
02
在赵丹的参考文献里,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朋友维舟2023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体制内的女性找对象越来越难》。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不是东北独有的现象,而是全国性的。即便是在东南沿海城市,体制内的女性找对象,也越来越困难。
这个问题开始偏离了婚恋问题,朝着性别议题跑了。因为在赵丹的调查中显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体制内女性的婚恋问题,比男性更加困难。
在维舟的文章中,所提到的观察,更多是在县域基础之上。也就是在县域的体制内女性,比在大城市中的女性找到对象的困难度更大。原因是在县域的范围之内,掌握资源的男性比大城市中更少,因此女性寻找到和自己“门当户对”的可能性就当然降低了。
维舟因此有一个论断:
在我看来,县城体制内女性找对象难,反倒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在这样的基层社会,也开始有新女性不愿意固守传统的婚恋模式,不肯将就,而坚持更高的婚恋质量和生活品质。问题不是她们“要求太高”,而是当地男性的素质整体低于女性,无法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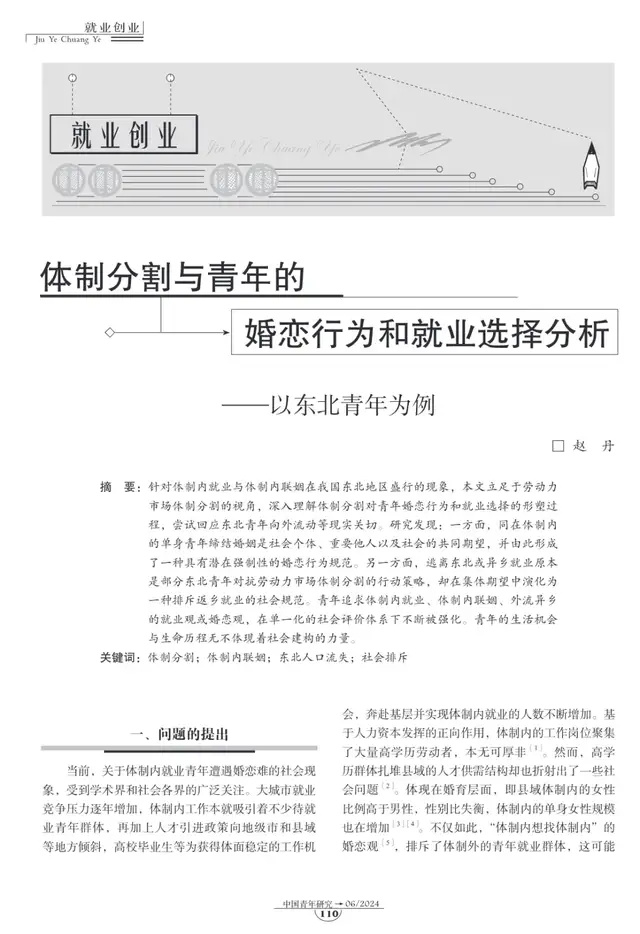
 相关论坛
相关论坛
 热门广告
热门广告
